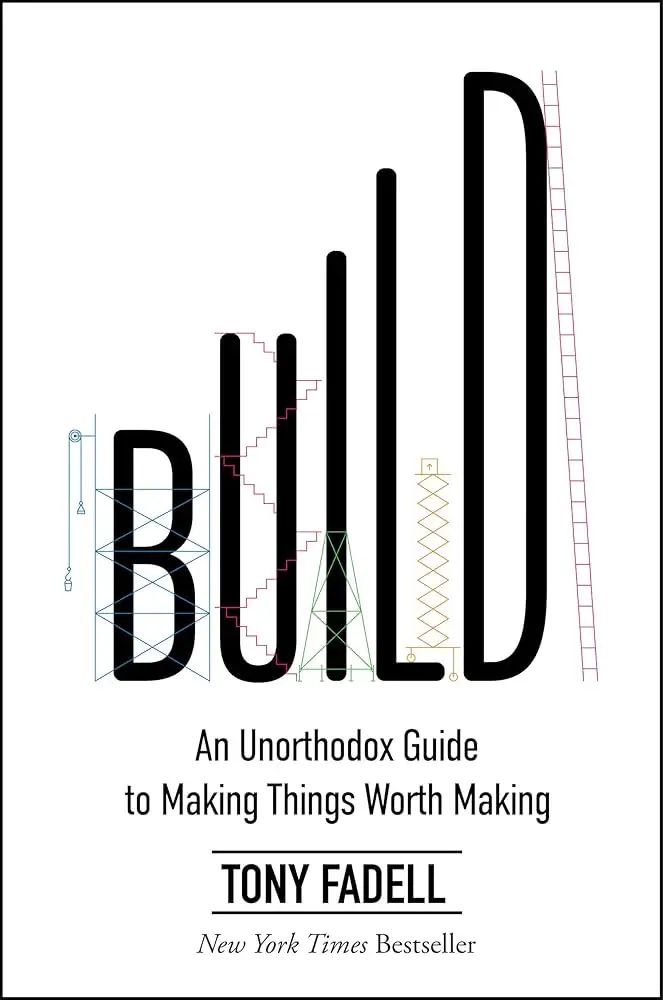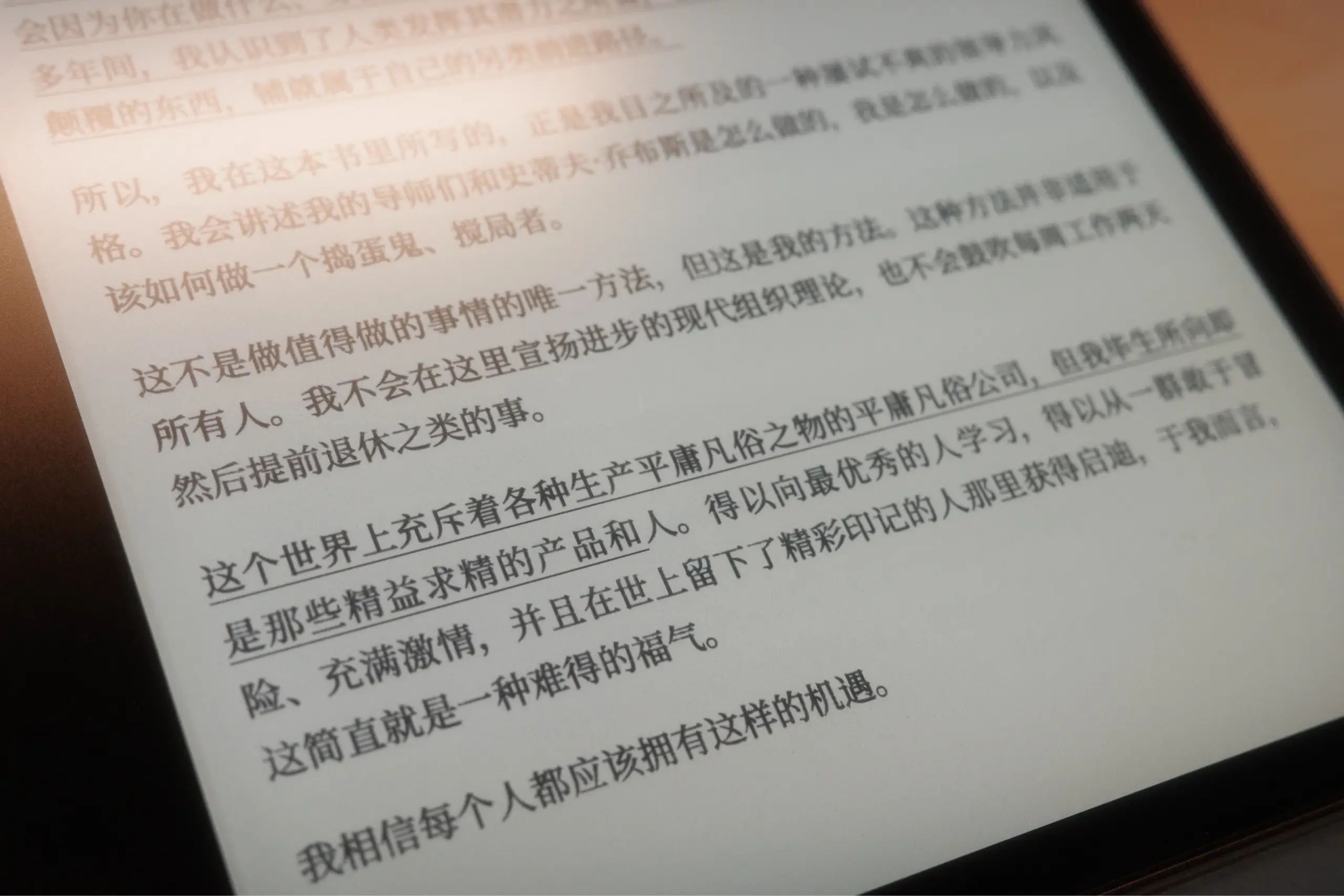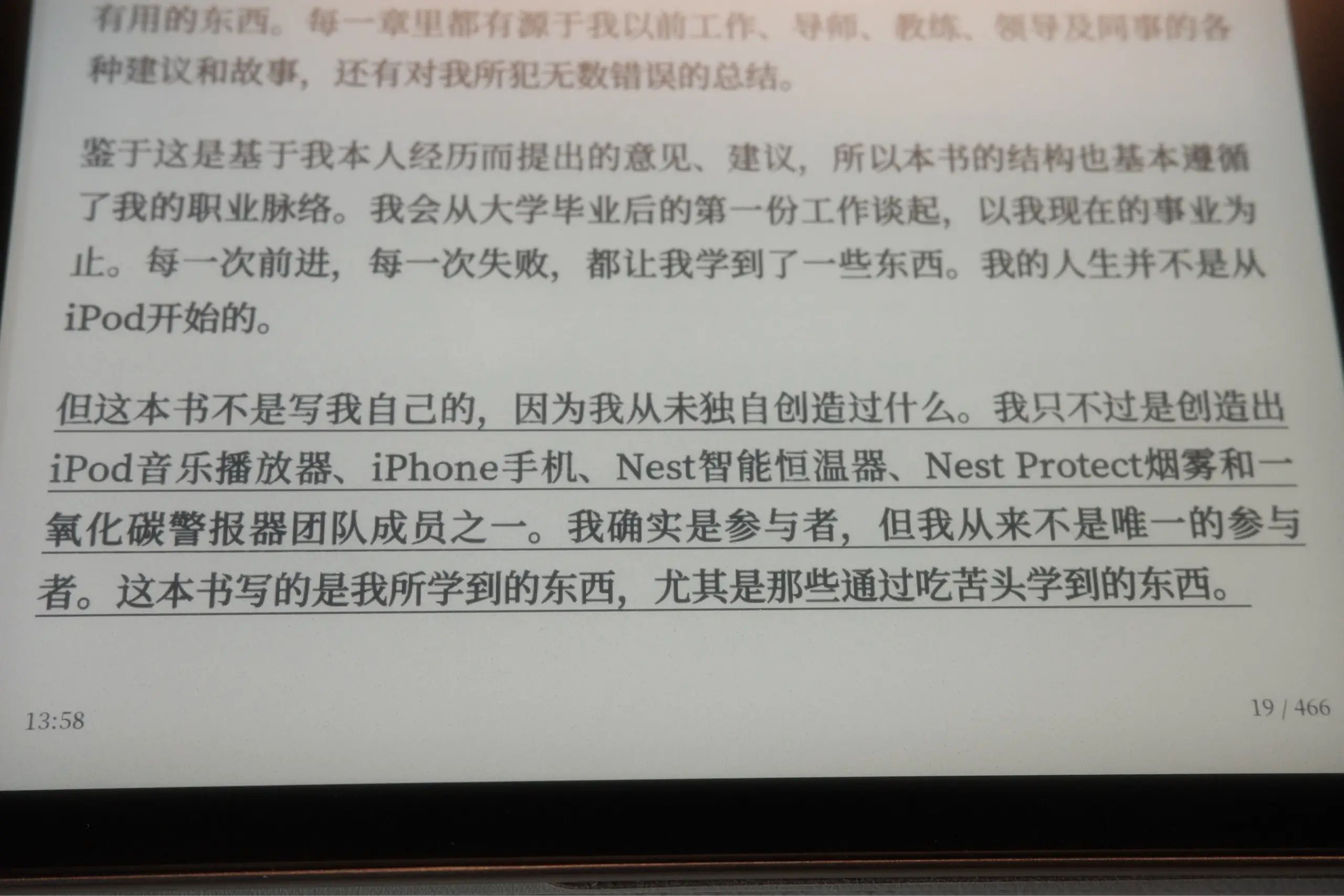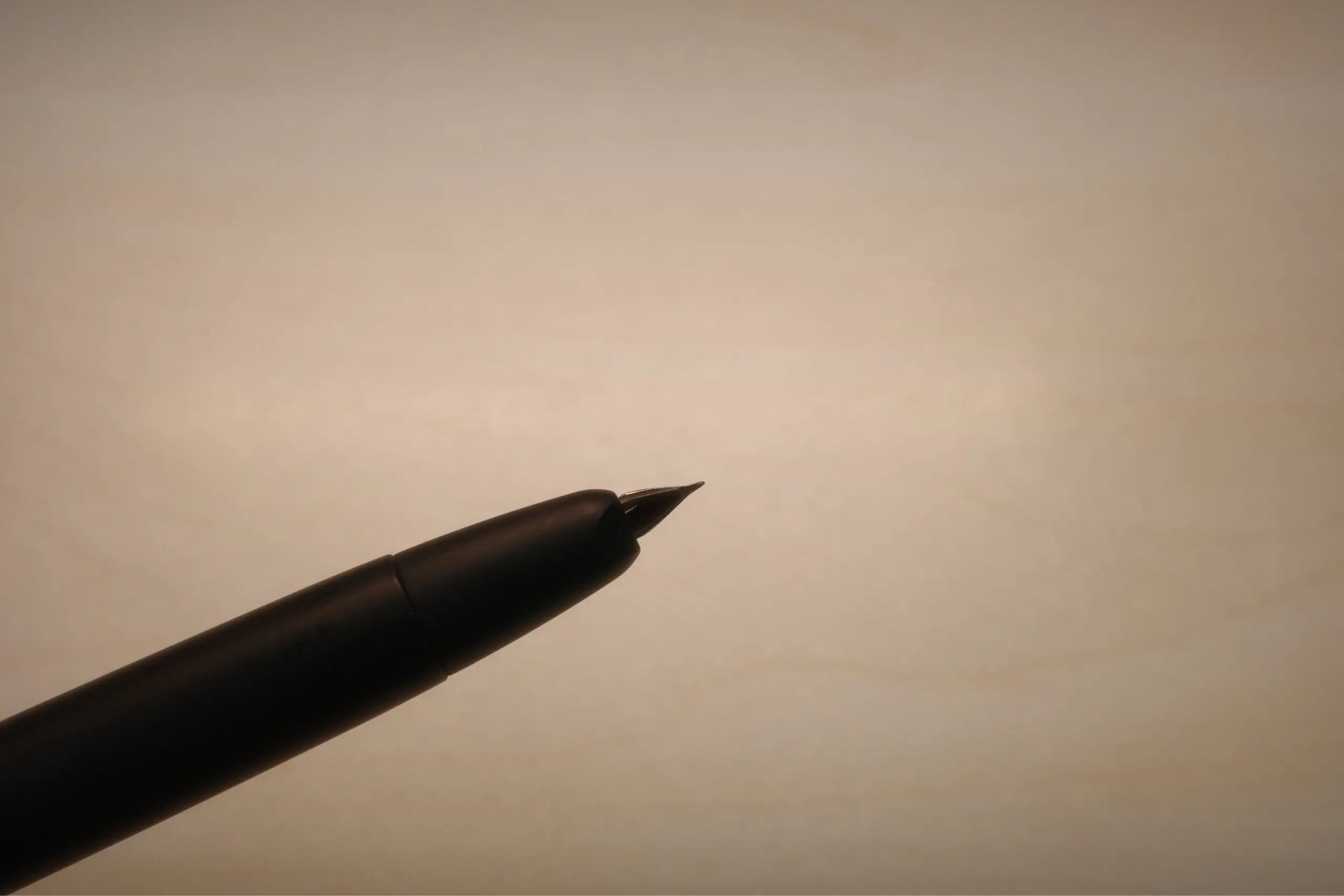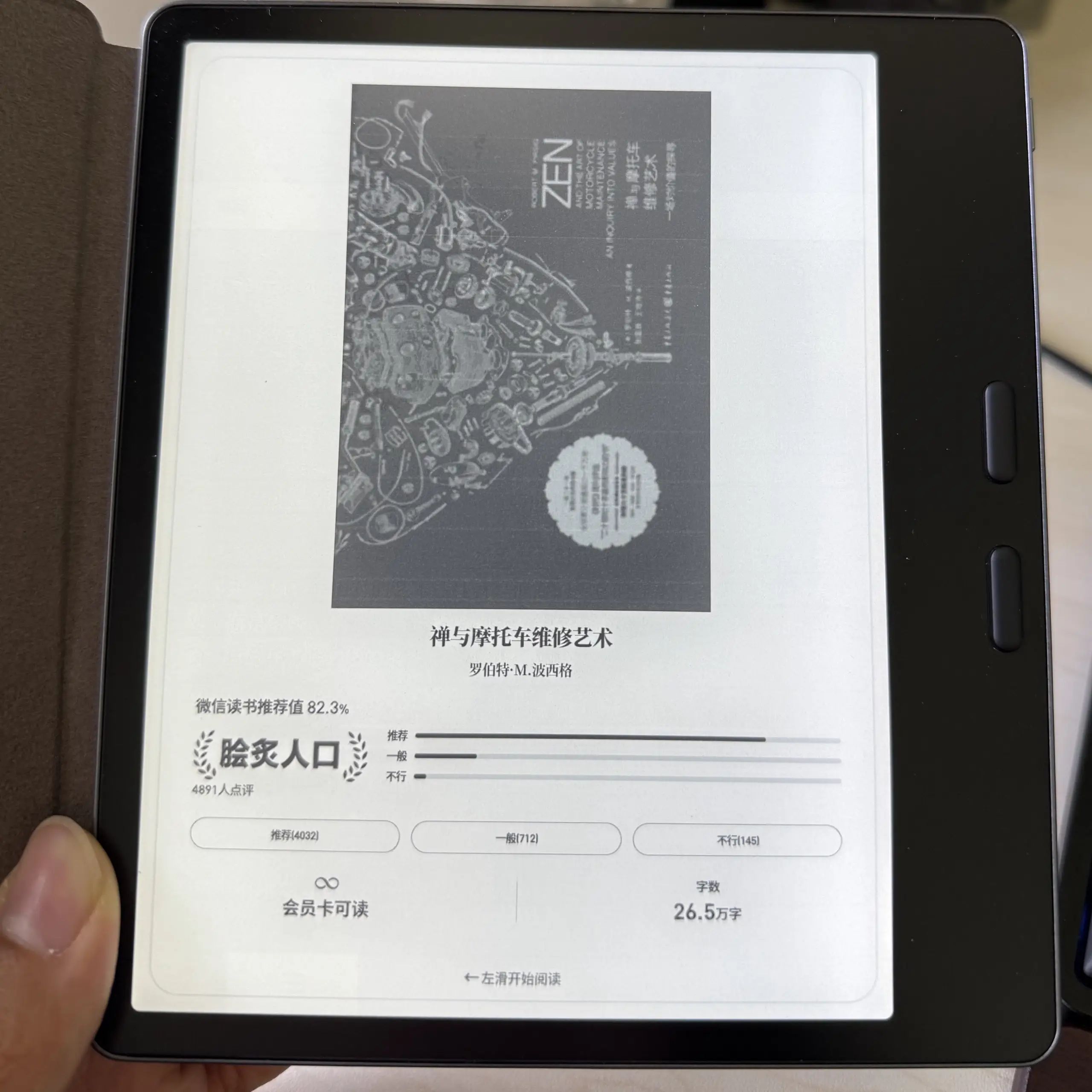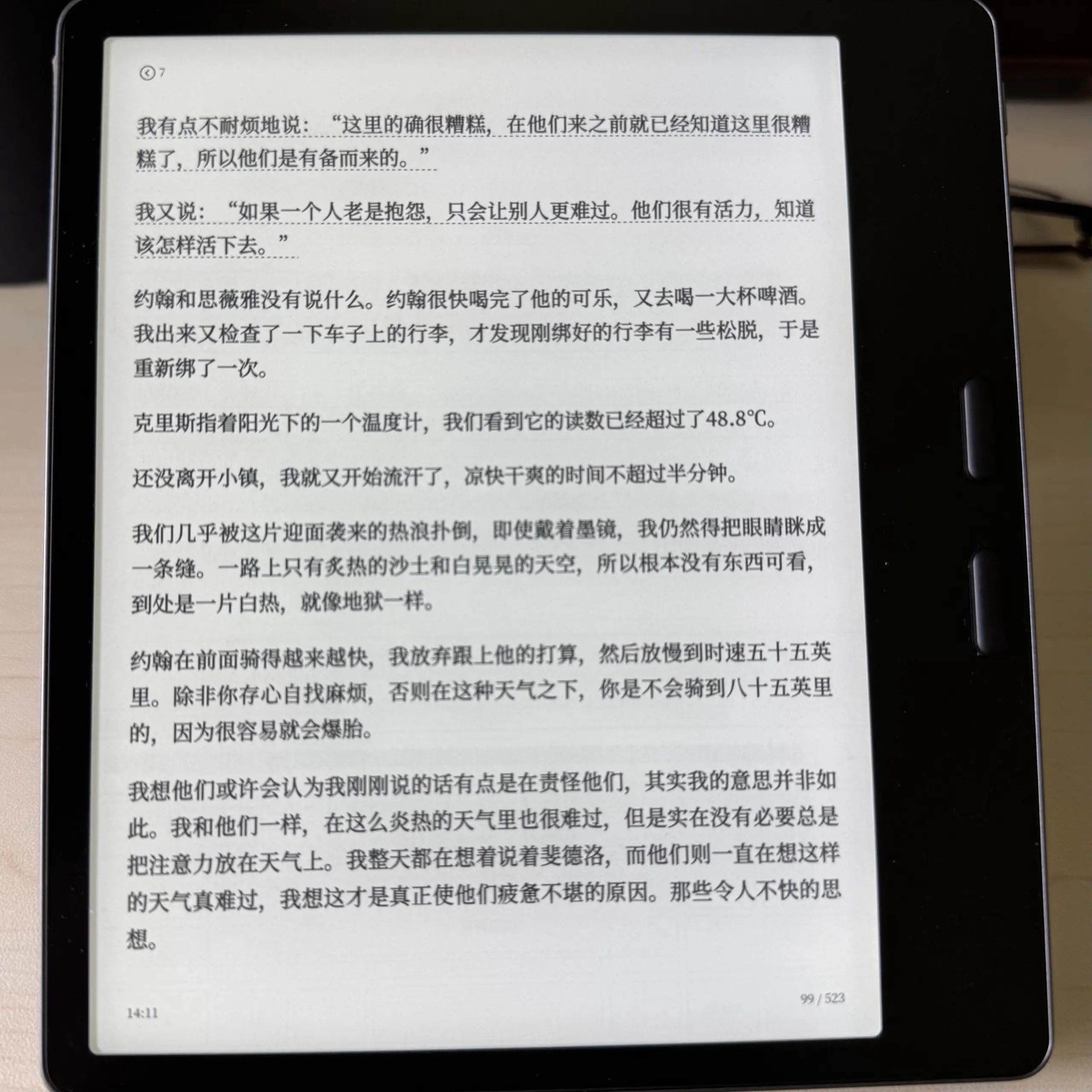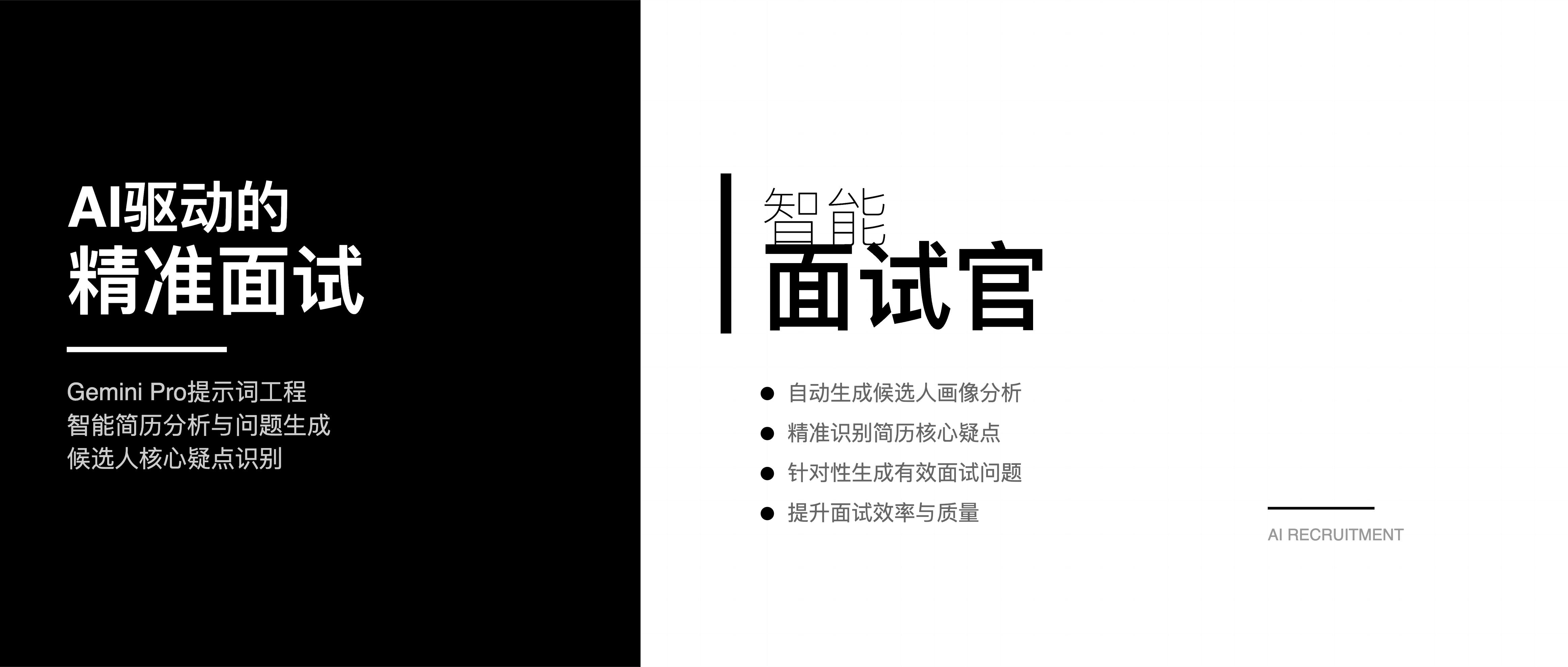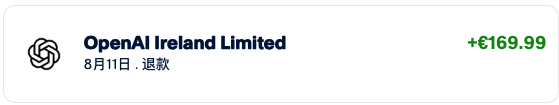历史哲学文本
附录C 诺斯替主义的中国热
直到19世纪,关于诺斯替主义的文献大都还是二手的,相关文献主要来自教父的反异端著作中的报道、概要和摘录,以及之后伊斯兰教的历史书和概要性纪录。不同时期的基督教史研究者或者哲学家,都根据自己的观点来阐释这个学派。在基督教会史中, 诺斯替主义被广泛的定义为异端。
1835年,鲍威尔(Ferdinand Christian Baur, 1792—1860年)出版专著《基督教的诺斯:或者其历史发展中的基督教宗教哲学》(Die Christliche Gnosis oder die christliche Religions-Philosophie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),基于黑格尔学说,将诺斯替主义阐释为基督教宗教哲学,强调了诺斯替主义哲学性的一面。而哈纳克<sup>[1]</sup>在《教义史》中说:
诺斯替主义者的做法,是试图对信仰予以原则规范,这即是基督教义的极度希腊化。<sup>[2]</sup>
又再度重复传统的观点,将诺斯替主义当成早期基督教的异端。
第一次世界大战后,对于这个教派的研究从教会史扩展为历史—宗教视野,一战、二战以来,世界剧烈变化,导致学者们看问题的视角及阐释方法均发生变化,对诺斯替主义的评论和看法,也引入新的元素<sup>[3]</sup>。后来的研究者,直指卡尔-巴特、别尔嘉耶夫、布洛赫(Ernst Bloch)、黑格尔、海德格尔、荣格、马克思、马塞尔(Gabriel Marcel)、梅烈日科夫斯基、尼采、施莱尔马赫、谢林、索洛维约夫、托尔斯泰、薇依等,他们身上均可以发现诺斯替游魂。1945年出土的《纳克·罕玛狄经书》(Nag Hammadi Library),为该教派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文献。<sup>[4]</sup>
从时代看,诺斯替主义属于基督教会被定义的最早期的诸种异端之一。对于经历了两千余年演变的基督教来说,到后期框架已经非常成熟,而早期的发展,无论是何种细小之处的分歧,都可能对日后的发展形成巨大的路径分歧。<sup>[5]</sup>诺斯替主义出现时,基督教义尚未成熟稳定,甚至相对于其他文化传统而言,教义还尚在修订演化之中,从而,与后来的教义比较,诺斯替主义表现出大量来自犹太、伊朗、巴比伦和埃及等东方传统的元素,比如说,教义的表达,采用了大量的神话形式,这些元素与希腊的观念以一种非常自由的形式混合。这种方式,更接近于一种原始宗教,而非一种信仰或者神学,从而于古典希腊思想和正统基督教信仰。一方面被基督教教父看成基督教信仰的异端,另一方面,又被新柏拉图主义者看成柏拉图哲学的异端。
诺斯替主义有三个基本特征:二元论、非宇宙主义、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同一的一元论。二元论来源于柏拉图(或源于摩尼教),认为世界和上帝的不同反映了一种异化的处境。非宇宙主义则推导出这个物质世界及其创造者都是无知的,从而是恶的观点。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的同一是诺斯替主义的最终目的,世界和创造它的上帝均需要被超越,而哪些被拯救的 属灵的人 要回归它的光明故乡,以使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恢复先前的同一。<sup>[6]</sup>作为完全的他者、异在者和未识者,诺斯替主义的上帝在其概念中更多的是否定而不是肯定。这三个基本特征,是诺斯替主义独立于希腊思想和基督教,并被确定为异端。
很明显,诺斯替主义的基本教义,会推导出一种非常极端的精英主义,这种精英主义自命为自己才是属灵者,而他者,都属于被毁灭的范围。按照这种思维逻辑,真理被认为是需要秘传的,<sup>[7]</sup>将 真理 弄成一种神神秘秘的武林秘籍,这就是诺斯替主义的 秘传和精英主义 特征。<sup>[8]</sup>
关于诺斯替主义在和其他教义竞争中的失败,刘小枫的看法是,与其说 因其教义中有绝对的二元论或是因其中有令人难以承负的恶的学说 ,不如说是因为其 秘传 的性质。所谓 秘传 ,就是仅仅为极少数人,而不是为大众写的书。 秘传 首先得有需要 秘传 的文本,这些文本必须是那些才、学、识都极其高超且德性超迈的人写下的。有了这样的文本,才有如何秘传的问题。秘传解经因其知识的门槛,而具有一种知识贵族或者知识精英主义的特征。而这种个体主义,必然
反对非属灵的、以等级方式建立并受到控制的大教会,
也即是说,反对基于普遍启示的言辞的教理和组织上的建制。<sup>[9]</sup>这意味着诺斯替主义教义上,是非教派,非建制,而具有遗世独立性质的。这种区分,进一步的,被列奥·施特劳斯解释为 哲人 和 先知 的区别。<sup>[10]</sup>哲人只满足于自己内心的批评家,而不向大众说话,因为哲人认为自己的思考是不可言说的。而先知,则面向大众演说。由此, 秘传的真理 和 精英主义 和 哲人 联系起来,三者合一,成为所言说的文本,具有武林秘籍性质的依据。
很吊诡的是,既然哲人所思考的是不可言说的,甚至只为自己而说,那么,哲人为什么还要说呢?既然是个人秘传的真理,诺斯替主义者为何又组成教派,而和其他教派竞争呢?既然是秘传的真理,为何哲人又汲汲于公开呢?为何哲人不遵循消极自由,而还努力于积极自由呢?
刘小枫的解释是:哲人的神圣使命就是思考更好的政治制度。于是,这极小一撮人自然而然可能形成一种秘密小团体,要成为这一团体的成员,就得知道隐藏自己的观点。因为这有双重的政治危险性,一是对百姓生活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否定,从而与其构成价值冲突;再有,哲人所思考的事情已经潜在地否定了现存政治制度的正当性,从而与现政权构成价值冲突。<sup>[11]</sup>为了避免被误会,也为了自身的性命安全,哲人就需要把自己的说辞分为公开的和隐微的。而隐微的真理,才是其言说的真正目的。
在列奥·施特劳斯和刘小枫的解释中,哲人的神圣使命就是思考更好的政治制度,这被当成所有立论的起点前提。但为什么哲人天生就要去思考政治呢?这么一种泛政治化的结果,是那些被认为曲线书写的文本,都被看成和政治有关。这一点,正是列奥·施特劳斯解经法和希腊哲学求真爱智的纯粹好奇的不同。希腊哲学是衣食富足的有闲阶级的遐思,而列奥·施特劳斯的解经,则是试图成为帝王师而不屑与平民来往的经世之才,因为言论与时代不符,而将言论重新包装,挂羊头卖狗肉的表达。也正是这种阴谋论形式,使得施特劳斯的解经,本身就具有一种装神弄鬼以获得权力的形式,也和中国传统的阴谋家很类似。这么一种解经说,对于经历过已经将意识形态冲突彻底的贯彻到每一个民众的运动中,将一切事件都已经彻底政治化的年代,<sup>[12]</sup>对于那些有志于独立思考,而政治则成为所有一切思考的话题和根源者,无疑是很合适的。<sup>[13]</sup>但对于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年代的学者来说,这种秘密解经法,便真正变成一种拉虎皮,扯大旗的宣传说法了,而很不幸的,则是那些被他们拿来重新解经的文本。
注释:
[1] 哈纳克(Adolf von Harnack),1851 — 1930年,德国新教神学家、教会史家。
[2] The attempt of the Gnostics to create an apostolic doctrine of faith and a Christian theology, or: the acute Hell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.
[3] 比如海德格尔的学生约纳斯,便纯粹从哲学观点,以存在主义、解释学、心理学进行诠释。
[4] 此书中译本《灵知派经书》,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。
[5] 混沌学说中有 蝴蝶效应 。
[6] 这个版本很类似倪匡一系列的科幻小说,以为地球上的人类,乃是从外星流放过来的囚犯,而那些经过救赎、洗净了的属灵者,才得以回到故乡,而地球上的不知悔改者,将被毁灭。
[7] 这一点,完全不同于科学体系成熟以后,真理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。
[8] 所以,相对于其他宗教力图去亲近大众,诺斯替主义表现出适合幻想者的神秘主义特征,也适合某些具有强烈自大倾向的幻觉者,类似的例子,比如《侠客行》中的白自在。
[9] 刘小枫,《真理为何要秘传》。
[10]
哲学与启示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。哲人追求自身的完善,先知无需追求善的知识,仅仅将自己看作上帝的仆人。这导致两种不同的实践方式,
众先知通常对人民、甚至对所有人讲话,而苏格拉底通常只对一个人讲话,(《耶路撒冷与雅典》,第20页)
先知与平民没有信仰冲突。哲人则必须是孤独的,他很像艺术家,只使他内心的批评家满意,当他试图取悦于听众时,他就失去了创造的感知。
转引自刘小枫《哲人与先知的世俗冲突》。
[11] 刘小枫举了一个例子:苏格拉底并不想威胁百姓和政府,但百姓和政府可不一定这么看,他的哲人生活方式本身实际上构成了威胁。
[12] 在这么一种年代,非此即彼,不是黑猫便是白猫,人被迫去划分阵营,被迫去站队,以表明立场。
[13] 刘小枫成长时的年代,正是一个这样的年代,所以很自然的将哲人的思考,归结以政治制度为其神圣使命也不足为奇。